

乡愁1983
雾气像是一层化不开的忧郁,严丝合缝地包裹着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古老小镇。俄国诗人安德烈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徘徊,他此行是为了寻访一位十八世纪俄国作曲家的足迹,身边还有一位美得令人窒息的意大利女翻译尤金伲亚。然而,即便身处如画的南欧风光,安德烈的心却始终像被一根无形的丝线拽着,越过国境线,沉入故乡那片潮湿、灰暗且宁静的旷野。 这种无法排遣的疏离感,让他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当美艳的尤金伲亚试图用现代人的热情去点燃他时,安德烈却转身走向了废墟和古堡。就在这时,他遇到了镇上著名的疯子多米尼克。这个曾把家人关在屋子里七年以躲避末日的怪人,在别人眼里是疯子,在安德烈眼里却是唯一的同类。多米尼克交给安德烈一个近乎荒诞的使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穿过那个干涸的圣凯瑟琳温泉池,且火苗不能熄灭。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耐心的考验,更像是一场赌上性命的祭祀。安德烈在破碎的现实和黑白的梦境之间反复横跳,他梦见故乡的妻儿,梦见那条总是在雨中奔跑的狗。他在异乡的泉水中寻找救赎,却发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种名为乡愁的绝症。当多米尼克在罗马广场上发表那番震耳欲聋的演讲并点燃自己时,安德烈也终于举起了那支脆弱的蜡烛,试图在风中完成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契约。

剧情简介
雾气像是一层化不开的忧郁,严丝合缝地包裹着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古老小镇。俄国诗人安德烈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徘徊,他此行是为了寻访一位十八世纪俄国作曲家的足迹,身边还有一位美得令人窒息的意大利女翻译尤金伲亚。然而,即便身处如画的南欧风光,安德烈的心却始终像被一根无形的丝线拽着,越过国境线,沉入故乡那片潮湿、灰暗且宁静的旷野。 这种无法排遣的疏离感,让他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当美艳的尤金伲亚试图用现代人的热情去点燃他时,安德烈却转身走向了废墟和古堡。就在这时,他遇到了镇上著名的疯子多米尼克。这个曾把家人关在屋子里七年以躲避末日的怪人,在别人眼里是疯子,在安德烈眼里却是唯一的同类。多米尼克交给安德烈一个近乎荒诞的使命: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穿过那个干涸的圣凯瑟琳温泉池,且火苗不能熄灭。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耐心的考验,更像是一场赌上性命的祭祀。安德烈在破碎的现实和黑白的梦境之间反复横跳,他梦见故乡的妻儿,梦见那条总是在雨中奔跑的狗。他在异乡的泉水中寻找救赎,却发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种名为乡愁的绝症。当多米尼克在罗马广场上发表那番震耳欲聋的演讲并点燃自己时,安德烈也终于举起了那支脆弱的蜡烛,试图在风中完成那个看似不可能的契约。
播放线路
观影点评
看这部电影不像是坐在银幕前,倒像是把自己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潭。塔可夫斯基并不打算讲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是在用时间当刻刀,在大银幕上雕刻灵魂的形状。如果你习惯了快节奏的感官刺激,可能会在电影开头的几个长镜头里感到迷茫,但只要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那些漫长的静止中,藏着一种能让空气凝固的张力。 电影里的光影对比简直是神迹,意大利的现实世界带着一种清冷的蓝灰色,而安德烈记忆中的俄国则是质感厚重的黑白。导演把乡愁拍成了一种生理上的病症,它不是简单的思乡,而是一个人精神根基断裂后的绝望。最让我震撼的是那个长达九分钟、几乎没有剪辑的运镜,安德烈护着那点微弱的烛火,在风中跌跌撞撞,火灭了就回去重来,那种对信念的近乎偏执的守护,看得人屏息凝神,仿佛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那根细小的蜡烛上。 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流亡者的电影,它更像是一首献给精神孤独者的长诗。它探讨的是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人类是否还能通过某种纯粹的仪式感,找回失落的完整性。当你看到片尾那个将俄国木屋与意大利教堂废墟融为一体的奇幻构图时,你会明白,有些人的灵魂注定是无法安放的,他们永远在路上,永远在寻找那个火苗不灭的瞬间。





 0
0 0
0 0
0 0
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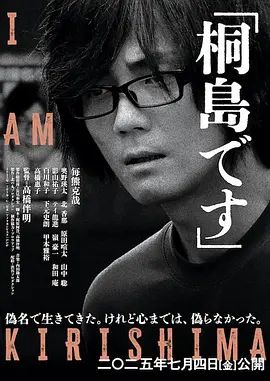 0
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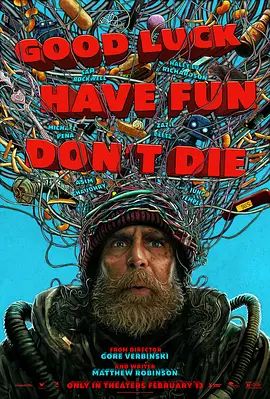 0
0